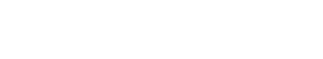一、案件全景扫描:从争议焦点到司法定论
(一)案件基本事实与争议焦点
高丙芳(山东某律师事务所主任,专职律师)涉嫌虚假诉讼案自一审开庭以来,便因案件性质的特殊性与律师执业风险的关联性引发法律界高度关注。据公开法律文书显示,公诉机关指控高丙芳在代理多起民商事案件过程中,明知当事人缺乏真实债权债务关系,仍协助其虚构借款合同、伪造转账凭证等关键证据,并以民事诉讼方式向法院提起诉讼,企图通过司法程序非法获取他人财产,涉案金额累计达数百万元。公诉机关指控,2019年高丙芳在代理75名农民工起诉工程总承包企业索要劳务费的系列案件中,明知农民工已实际获得报酬,仍协助包工头米某某、陈某某伪造劳务合同、工资欠条等证据,虚构265万余元的债权债务关系,通过民事诉讼程序非法索要工程款。一审、二审法院均认定其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罪,并结合其在证据制作、诉讼推进中的具体作用,判处相应刑罚。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24年12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高丙芳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高丙芳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由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25年6月17日,该院作出二审裁定,维持原判。二审法院在裁定书中明确指出,高丙芳在代理案件过程中存在主观明知证据伪造、积极参与诉讼材料提交及庭审陈述引导等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罪。
案件的核心争议点集中于:一是高丙芳对当事人虚构事实的主观明知程度;二是其在证据制作与诉讼推进过程中的具体行为是否构成“帮助伪造证据”或“提起虚假诉讼”;三是民商事代理行为与刑事犯罪的法律边界界定。
(二)二审维持原判的司法逻辑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现有证据能够充分证明高丙芳在代理案件时,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系伪造、法律关系属虚构的事实存在主观明知,且其积极参与了证据的制作、诉讼材料的提交以及庭审陈述的引导等行为,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民商事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士,肩负维护司法秩序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双重职责,若为追求诉讼结果而突破法律底线,必然要承担相应的刑事法律后果。”二审维持原判的结论,不仅对个案作出了最终司法定论,更向整个律师行业传递了法律红线不可逾越的强烈信号。
二、行业反响与深层思考:民商事律师的刑事风险困局
(一)律师同行的关注与声援背后
案件审理期间,多地律师协会及行业组织通过不同形式表达了对案件的关注,部分律师自发形成案件研讨小组,围绕“律师执业风险边界”“民刑交叉案件代理策略”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这种行业性的集体关注,反映出律师群体对自身执业安全的焦虑——当民商事代理行为可能触及刑事风险时,如何在维护当事人权益与遵守法律底线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亟待解决的行业共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声援行动并非单纯为个案结果呐喊,更多是借此推动行业对执业风险防控体系的反思与构建。
(二)民商事律师刑事风险的严峻现状
与公众认知中“刑事律师风险更高”的印象不同,事实上民商事律师面临的刑事追责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至2024年间,全国法院审理的虚假诉讼犯罪案件中,涉及律师参与或协助的比例约占32%,其中绝大多数为民商事领域案件。从罪名分布看,《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虚假诉讼罪、《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二款帮助伪造证据罪、《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妨害作证罪构成“三大风险罪名”,而《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拒执罪在执行阶段的代理过程中也逐渐成为新的风险点。这种风险现状的形成,本质上源于部分律师对“诉讼策略”与“刑事违法”的边界认知模糊,将“钻法律空子”误读为“专业能力”,最终酿成执业危机。
三、风险防控体系构建:从理念更新到行为规范
(一)建立“刑事风险预判”工作机制
1.案件受理阶段的风险筛查
民商事律师在接案时,应当建立严格的刑事风险评估清单,对以下情形保持高度警惕:当事人要求“制造”证据以弥补事实缺陷的;涉案法律关系明显不符合常理或交易习惯的;对方当事人人数众多且分散、证据材料异常齐全的;当事人承诺“高比例胜诉酬金”但拒绝说明案件真实背景的。例如,在借贷纠纷案件中,若当事人无法说明借款来源、利息约定方式等基本事实,且要求律师协助完善借款合同条款,此时律师应当立即启动风险预警程序,而非盲目承接案件。
2.证据审查的“实质真实性”原则
突破传统“形式审查”局限,对证据来源、法律关系真实性保持“实质审查”意识,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实行“三核”制度:
核来源(要求当事人说明证据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必要时提供原始载体);
核逻辑(分析证据内容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是否符合客观规律);
核矛盾(对比不同证据之间是否存在无法解释的冲突)。
以高丙芳案为例,若其在代理时对当事人提供的大额现金借款转账凭证进行实质审查,核实资金流水的真实性与关联性,或许能够避免陷入刑事风险。
(二)规范代理行为的“三项铁律”
1.谈话笔录的“法律告知+责任划分”双轨制
制作谈话笔录时,必须包含以下核心内容:一是向当事人明确告知“虚假诉讼、伪造证据的法律后果”,并要求当事人签署《法律风险知悉确认书》;二是详细记录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证据来源及证明目的,对当事人提出的“特殊代理要求”(如“能否想办法让对方认账”)进行重点标注;三是明确约定“若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据或隐瞒重要事实,律师有权单方解除代理合同并保留追责权利”。这种规范化的笔录制作,不仅是防范风险的证据留存,更是对当事人的法律警示。
2.证据原件的“有限接触+复核留痕”管理
原则上不直接保管当事人证据原件,确需接触时应当履行严格的交接手续,制作《证据原件接收清单》,注明接收时间、证据名称、数量、特征等信息,并由当事人签字确认。对关键证据(如合同、权属证书、转账记录等)的复核过程,应当形成书面《证据复核意见》,记录复核方法、发现的问题及当事人的解释说明。对于存在明显瑕疵或疑点的证据,应当明确告知当事人“该证据可能无法被法院采信,甚至可能引发法律风险”,并建议其通过合法途径补充完善证据。
3.代理策略的“合法性优先”决策机制
在制定诉讼策略时,必须遵循“三问”原则:
一问是否有事实依据(是否有真实的法律关系基础);
二问是否有法律依据(策略选择是否符合实体法与程序法规定);
三问是否有道德风险(是否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
例如,在选择诉讼主体时,应当基于真实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定原告与被告,而非为了便于执行而“虚构”当事人;在确定诉讼请求时,应当根据实际损失提出合理主张,而非通过夸大损失、虚增金额等方式谋取不当利益。
(三)构建“跨专业协作”风险防火墙
1.重大疑难案件的刑事法律“会诊”
对于法律关系复杂、涉及金额巨大或存在明显民刑交叉特征的案件,应当主动寻求刑事法律专业人士的协助,建立“民商事代理+刑事合规”的双团队服务模式。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在案件受理前,邀请刑辩律师对案件进行“刑事风险体检”,出具《刑事合规审查意见》;二是在代理过程中,就证据合法性、行为性质等问题与刑辩律师保持定期沟通,必要时召开案件研讨会;三是在诉讼策略制定后,由刑辩律师对策略的刑事风险系数进行评估,确保不触及法律红线。
2.行业内部的“风险案例”共享机制
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执业风险案例库,收集整理本所及行业内发生的风险案例,定期组织学习讨论。通过分析案例中的“风险点识别”“违规行为演变”“司法裁判逻辑”等内容,提升律师的风险敏感度与应对能力。例如,针对高丙芳案,可以重点分析“律师在证据制作环节的具体行为如何被认定为‘帮助伪造’”“主观明知的证据如何形成链条”等问题,为律师提供直观的风险警示。
四、行业自律与制度完善:从个体防控到生态优化
(一)律师协会的风险预警与合规指引
律师协会应当充分发挥行业自律作用,构建多层次的风险防控体系:一是制定《民商事律师刑事风险防控指引》,明确代理各环节的合规要求与操作标准。明确要求律师在代理案件时,需严格遵循《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及《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证据来源、法律关系真实性保持“实质审查”意识,避免因追求胜诉结果而突破法律底线。二是建立“风险案件”报告制度,要求律师事务所对可能涉及刑事风险的案件及时报备,以便协会提供专业指导;三是开展“刑事合规”专项培训,将刑法基础知识、风险案例分析纳入律师继续教育必修内容,提升律师的刑事法律素养。
(二)司法机关与律师行业的“良性互动”
建议司法机关与律师协会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通过以下方式共同防范刑事风险:一是定期发布“民商事代理刑事风险典型案例”,明确法律适用标准与裁判尺度;二是在办理涉及律师的刑事案件时,充分听取律师协会及辩护律师的意见,确保案件处理既严格执法又兼顾行业特性;三是联合开展“法律职业共同体”专题研讨,就民刑交叉案件的代理边界、证据标准等问题达成共识,减少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
五、结语:在专业与底线之间寻找执业平衡
高丙芳案的最终判决,为整个律师行业敲响了警钟。民商事律师的执业风险并非遥不可及,而是潜藏在每一个案件的代理过程中。规避刑事风险,不仅是对律师个人执业安全的保护,更是维护司法公信力、推动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正如一位资深刑辩律师所言:“优秀的民商事律师,应当同时具备精湛的民事代理技能与敏锐的刑事风险意识,在追求当事人合法权益最大化的同时,始终保持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唯有如此,才能在复杂的法律实践中,既彰显专业价值,又坚守法律底线,实现律师职业的可持续发展。
免责声明:本网部分文章和信息来源于国际互联网,本网转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和学习之目的。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立即联系网站所有人,我们会予以更改或删除相关文章,保证您的权利。